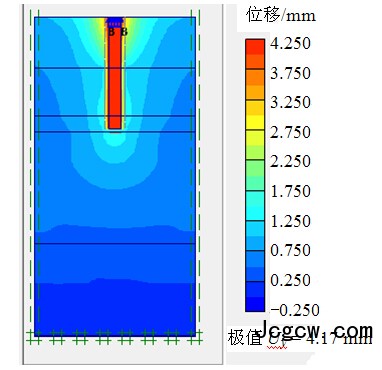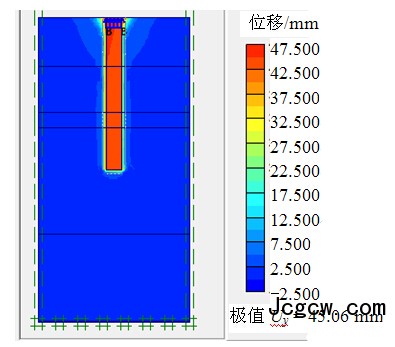|
土层
|
层厚
/m
|
重度
/(kN/m3)
|
内摩擦角j/(°)
|
黏聚力c/kPa
|
桩土侧摩阻力
t/kPa
|
|
①杂填土
|
3.2
|
16
|
19
|
8
|
35
|
|
②卵石
|
3.0
|
21
|
40
|
5
|
150
|
|
②-1细砂
|
1.0
|
18
|
30
|
5
|
40
|
|
③强风化层
|
7.0
|
19
|
22
|
25
|
100
|
|
④中风化层
|
12.0
|
22
|
30
|
28
|
120
|
|
⑤微风化层
|
18.0
|
24
|
32
|
35
|
140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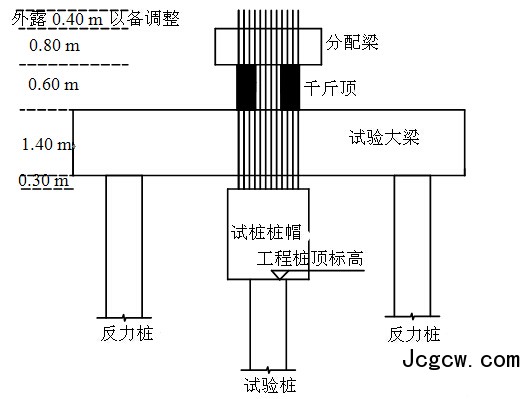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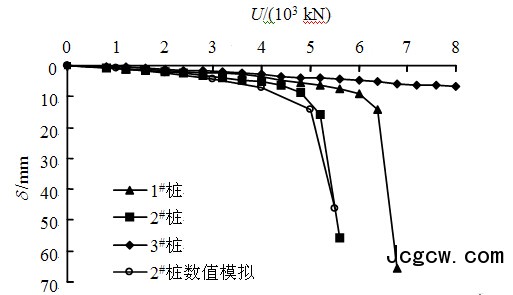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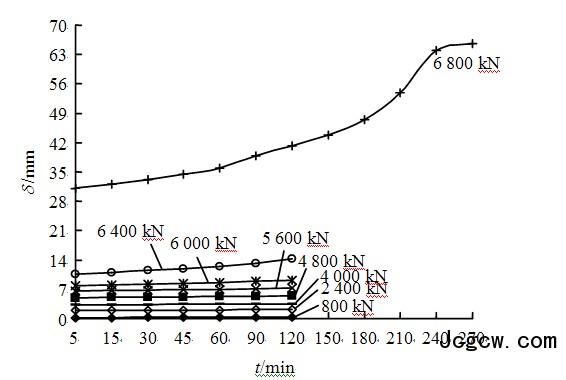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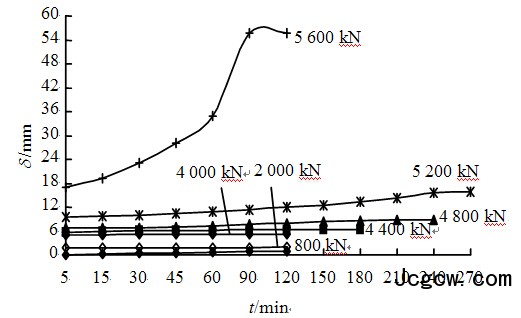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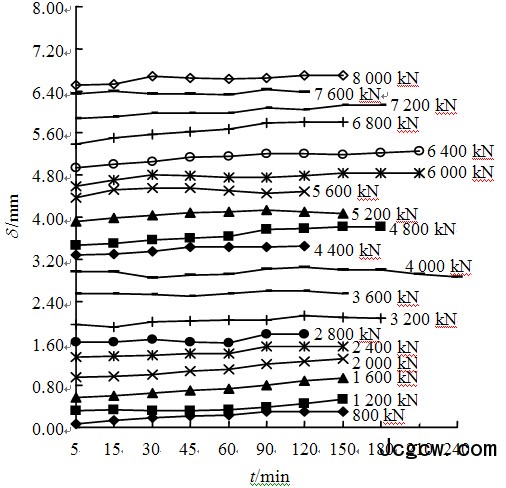
|
桩号
|
最大加载/kN
|
最大上拔量/mm
|
回弹率/%
|
|
1#桩
|
6 800
|
65.68
|
21.45
|
|
2#桩
|
5 600
|
55.80
|
19.61
|
|
3#桩
|
8 000
|
6.69
|
32.77
|
|
4#桩
|
8 500
|
7.50
|
42.10
|
|
5#桩
|
8 500
|
6.25
|
38.40
|
|
6#桩
|
9 060
|
10.24
|
41.89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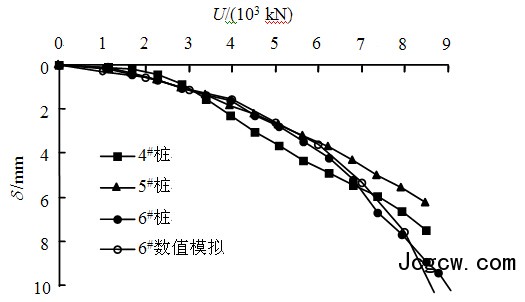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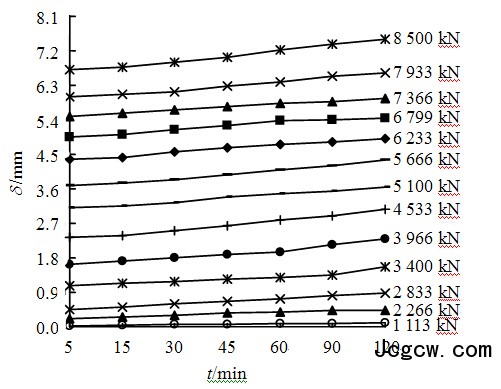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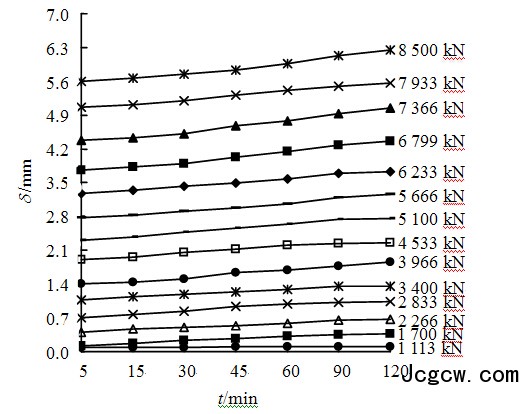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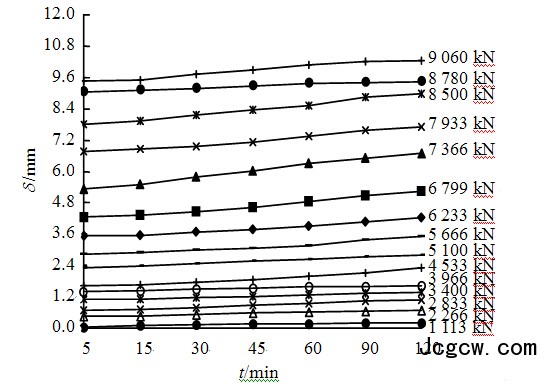



|
桩号
|
函数模型型
|
模型参数
|
拟合精度
|
实测极限荷载
/kN
|
预测极限荷载/kN
|
||
|
1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4 676, b = -0.672 3
|
0.990 9
|
6 400
|
6 363.6
|
6 473.8
|
6 549.3
|
|
指数函数
|
a = 4.672e-008, b = 0.003 096
|
0.948 2
|
6 096.6
|
6 168.6
|
6 227.5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179.5, b = 20.82
|
0.945 3
|
6 340.0
|
6 408.0
|
6 465.0
|
||
|
2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2947, b = -0.5082
|
0.995 0
|
5 200
|
5 163.8
|
5 279.5
|
5 359.5
|
|
指数函数
|
a = 4.011e-005, b = 0.002 523
|
0.957 9
|
4 803.7
|
4 892.1
|
4 964.4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115.3, b = 13.82
|
0.952 7
|
5 133.8
|
5 217.4
|
5 286.7
|
||
|
3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1608, b = -0.058 18
|
0.993 3
|
13 324.5
|
14 864.1
|
16 104.7
|
|
|
指数函数
|
a = 0.9193, b = 0.000 262 8
|
0.946 7
|
11 719.5
|
12 568.6
|
13 262.3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9.34, b = 1.255
|
0.996 3
|
15 544.6
|
18 569.4
|
19 427.9
|
||
|
4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2182, b = -0.127 8
|
0.972 4
|
12 272.2
|
13 003.6
|
13 541.6
|
|
|
指数函数
|
a = 0.670 4, b = 0.000 294 2
|
0.936 5
|
11 541.9
|
12 300.3
|
12 920.0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12.53, b = 1.61
|
0.988 1
|
15 418.3
|
17 710.5
|
19 834.0
|
||
|
5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2811, b = -0.175 7
|
0.991 9
|
12 454.6
|
13 032.0
|
13 447.6
|
|
|
指数函数
|
a = 0.661 5, b = 0.000 267 6
|
0.959 9
|
12 739.1
|
13 527.9
|
14 254.3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13.03, b = 1.644
|
0.999 3
|
17 120.2
|
18 609.0
|
19 908.2
|
||
|
6#
|
双曲线函数
|
a = 277 2, b = -0.211 7
|
0.992 2
|
10 592.3
|
11 013.1
|
11 312.7
|
|
|
指数函数
|
a = 0.996 5, b = 0.000 164 1
|
0.998 1
|
10 375.6
|
11 988.3
|
12 284.1
|
||
|
幂函数
|
a = -17.69, b = 2.196
|
0.997 9
|
12 329.3
|
13 647.9
|
14 829.5
|
||